
昨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从天文学上来说,这是一年中白昼时间最短的一天。偏偏按照旧习俗,这一天大家要赶在天黑之前都回到家,因为这一天也是全年中阴气最重的一天,天黑之后再继续在外面晃悠,难免不吉利。但是天黑之前就猫在家里的做法,也只适合农业时代农闲季节的农民,对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来说,哪怕能在“晚五”时分准时下班,天色也已经乌漆抹黑。不过,拜笼罩大半个中国的重污染天气所赐,当天凡是出来活动的鬼,也都会两眼昏黑找不到人,并迷失和融化在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雾霾当中,所以,大家也并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虽然,下午5点就天黑确实有些不爽,但是相比而言,上海还处于地区上的中低维度地区,冬至日前后的昼短夜长现象应该说还不算太显著。小编有个同学在英国念书,曾抱怨说他们那个鬼地方,圣诞节前后每天要到早上9点多种才天亮,然后下午3点过后天就完全黑了,再加上英伦三岛常见的雨雪雾天气,要在冬天见到太阳公公的脸还真不容易。于是,一到了冬天,心理诊所门前就排满了去看抑郁症的人群。甚至,本来挺开朗的人,这时候也会整天唉声叹气起来。医学界给出的解释便是,长期照不到太阳会严重影响人的内分泌平衡,导致精神不振。对此,之前曾经上了N年夜班的小编本人只得暗暗感叹一声:真是伤不起……
但毕竟,冬至这一天之后紧邻着的便是圣诞和新年假期,所以,大家或许还是有一个让自己稍微开心一下的理由。而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是欧美金融市场除了夏天之外的又一个淡季,许多交易员从这周一便开始享受休假,金融市场基本进入了交投清淡的“巡航驾驶”状态,坚持在岗工作者在节日临近时,也多少会有些心不在焉。这可不,美国商务部的值班人员就在当地时间周二晚上错误地发布了本来该到周三早晨才应该发布的美国11月个人支出数据,虽然对市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也算是重大失误了。不知道美国那边会不会也有专门用来背黑锅的“临时工”角色……
不光是洋节将至可以让大家兴奋一下,按照东方传统,也有“冬至大过年”一说。因为冬至节气其实是农历推算的起点,从这一天起,白昼时间一天比一天长,而“数九寒冬”也以冬至日为起点,数万九九八十一天,大家便能迎得冬去春来。这一天在古代也是皇帝祭祀天地的日子,皇家仪仗队会浩浩荡荡从紫禁城向天坛开拔,京城百姓也可以趁机一睹圣上的龙颜,好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汽车尾气,没有雾霾阻挡大家的视线,街上顶多也就有“马尾气”带来的些许污染而已。
而贵为“天子”要在这一天祭天,那么升斗小民也就得祭祀各自的祖先。于是,冬至当天也就成了除了清明节之外的又一扫墓高峰。由于墓地大多建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外,在扫墓路上的来回奔波,也成了一桩苦差事,尤其是在遭遇集中祭扫高峰,路上堵成一团的时候。但既然大家缅怀先人的情感如此深切,当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之所以墓地都在远离市区的郊外,还是因为城市土地寸土寸金,上海市区的土地楼板价就高达每平方米6-7万元,而公墓又不像公寓,可以造成多层的在垂直方向叠起来节约土地成本,于是,一座占地1.5平方米的最简单的墓,成本价就高达10万元以上,这只能让大家惊呼“死不起”。其实,就算是不差钱的土豪,也不能把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家”安在闹事中心区,因为一旦这样,你的邻居都会和你急——虽然那个小小的盒子人人最后都要住进去,但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中国人希望它出现在自己的身边……
无论如何,坟墓在东方文化中都是不吉利的存在,这和儒道文化下贪生恶死的民族心理不无关联。许多在宗教熏陶下的民族所追求的是百年之后在彼岸世界获得永生,而孔夫子却告诉大家“未知生,焉知死?”,道家信徒更是追求如何让自己在今世世界长生不朽,于是,死亡问题就成了汉民族的最大忌讳。这和西方人面对这一问题的坦诚构成了鲜明的反差。小编早年在澳大利亚,就曾见到大片的公墓区直接坐落在闹市中心,一街之隔便是繁华的火车站和商业区,似乎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忌讳。后来,玩了一款叫做《模拟城市》的游戏,发现里面的“市政府”顾问隔三差五就会提醒是否需要免费扩建公墓建筑,结果的按照思维定势,小编把公墓全都仍在了偏远的郊外,和垃圾填埋场与有毒化工厂为邻,后来才发现,这个游戏是按照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设计的,公墓不但不会降低周边低价,还因为其高绿化率和安逸静谧的环境,能让周围的普通建筑摇身一变成为豪宅……唉,文化差距,就是伤不起。
所以,在民间迷信风气盛行的广东潮汕地区,曾经还发生过一件咄咄怪事,一栋政府投资的新建筑被谣传为新建的殡仪馆,于是周边居民对此大为抗议,甚至围攻当地政府。而在政府人员出面解释说,那根本不是什么殡仪馆,只是污水处理厂时,抗议人群立刻就做鸟兽散。对亡灵的恐惧超过了有形的物质污染,这也堪称一绝。不过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中国式葬礼上免不了的是鬼哭狼嚎和吹吹打打,这噪音就够人受了。而扫墓日上坟人群焚烧纸钱香烛,却又为PM2.5贡献了额外力量。虽然,今年冬至上海各大墓园管理方一再强调上级精神,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和焚烧迷信用品,但是要改变巨大的习俗力量,却还任重道远。如果那一天大家也能安安静静送别故人,怀着平和肃穆的心情祭扫祖坟的话,那么自然也会有人选择在墓园旁边安家的。
但虽然大家不愿住在坟场旁边,却也要正视“逝者如斯夫”的事实。上海每年新增逝者10多万人,按上文所计算的每人1.5平方米的墓穴面积计算,一年就要有一个人民公园那么大的面积被辟为公墓。所以,一直有关于如何解决“死人与活人争地”这个问题的争论。而事实上,上海人的墓地范围早就延伸到了周边省份,尤其,每到清明冬至,公路上就会挤满开往苏州方向的车流。鉴于苏杭在地理经济上被视作上海的“后花园”,于是墓地在售卖墓穴时,打出的广告语也是“人生后花园”,这怎么听来都让人觉得有些不舒服……而登峰造极的状况就是,苏州郊外太湖边太平山下景色秀丽的木渎镇,因为成为了太多上海人置办身后“物业”的首选地,已经快要改名叫做“墓渎”了……
所以,紧缺的墓葬用地和加速老龄化导致的每年水涨船高的逝者人数,就使得墓地的价格水涨船高,就算墓地在偏远的郊外,每平方米的单价甚至也超过了市中心的公寓。于是,大家就抱怨说,除了二胎“生不起”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棘手的“死不起”问题。所以,和“经济适用房”对应,现在还有“经济适用墓”这样的概念,号称只需数千元,就能让先人入土为安,但是有效期只有20年,时间到了,恐怕还得请墓主把位子腾出来,将空间让予后来者……
其实,担心身后居所的往往是升斗小民,因为大家明知“死去元知万事空”,却也还希望能留一块地让子孙能记得自己。而越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在这个问题上反而越是豁达。政界、商界甚至宗教界的许多高人,往往却都选择火化之后把自己的骨灰一撒之,不留墓碑,因为自己既然已经青史留名,何苦还要把名字刻在石头上让大家纪念呢?所以,大家就也姑且以此为人生奋斗目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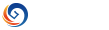


 美城
美城






 沪公网安备 31010702001056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702001056号